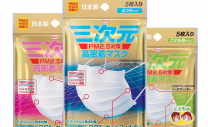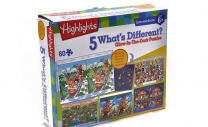一、思考
如今,有很多人提倡复兴国学。
提到国学,一定绕不开儒家,绕不开孔子;孔子最可靠的学说思想在《论语》中,一时间《论语》也成为国学启蒙中的必修科目。
《论语》该怎么学呢?
有些人搬出了“古人”的方法,从最开始的“中华正音”,到后来的“吟诵”,许多都主张读诵,而于意思却不求甚解,即使讲解,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照着注释念一遍解释,只顾读得煞有介事,若问问意思,却一脸茫然。
这与“鹦鹉学舌”何异?
主张这样方法的人,爱用一句“古人方法”搪塞,或者用一句“将来有用”敷衍。
《论语》历史悠久,历代学习方法或有不同,这种主要依靠声音读诵,而不求义理探究,究竟是所有古人的公法,还是某朝某代的一时之法?即便是古人普遍的方法,我们就可以不问缘由地模仿吗?
而“将来有用”,将来究竟有多大用?是今天花了一分力,将来有一分效,还是今天花十分力,将来有一分效?
《论语》中明明写着“学而不思则罔”,而今日教《论语》者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“不需理解,只需读”?
唐代韩愈即明言:“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……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,或不焉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”
而南宋朱熹也说:学《论语》要“虚心涵泳,切己省察,句句从自己身上看过”,“不求诸心,故昏而不得,不习其事,故危而不安”。
近人钱穆道:读书要“注意于书中之人物、时代、行事,使书本有活气”,“注意于书中之分类、组织、系统,使书本有条理”,“注意本书于我侪切身切世有关系之事项,使书本有应用”。
而胡适说得更简洁:要“研究问题”。即我们不应学空话,而应放到具体问题上讨论。
二、思辨
今日学国学,常有一个奇怪的论调,即不许质疑。认为一旦质疑,即是对圣人不敬。
古人早说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,我们学前人的经典,非但要理解,而且要有取舍。
近人冯友兰道:“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,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,但是,除此之外,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。”
哪些只是具有“一时的意义”,哪些却是具有“持久的意义”?现代的国学教育,是否也应当做一番梳理呢?
冯先生进而说:“如果认为,五种伦常关系的某些内容已经失去时效,因此儒家的人生理想应当全部抛弃,这显然是错的。反过来,如果因为儒家的人生理想应当保持,从而认为五种社会关系也不应改变,这显然也是错的。”
故而,如果我们不做这一番筛选,总是一股脑儿抛弃或者一股脑儿接受,全盘抛弃固然可惜,全盘接受不也有害吗?
当代学人傅佩荣道:“文化分三个层次,第一个是器物,第二个是制度,第三个是理念”。我们参照这个分类可以看到:《论语》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书,二千五百年间的变化不可谓不小,然而相较而言,理念方面变化较小,制度方面变化较大,而器物方面更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故而钱穆先生总结道:“孔子既为二千五百年前之人物,则其学说思想,不免为二千五百年前人设想;其不能一一通用于今日,自无待论;又其与门弟子讲诵,因材施教,变化无方,今亦不能一体信奉以为科律也明矣……道随人生之不同而变……我侪之人生,我侪当自谋之。”
打破中西文化壁垒,打通传统现代隔阂,打开4000年中华文明视野,做思考的启蒙,做理解的国学!
我们新开设:国学晚托班、《论语》精读、《史记》与《古文观止》,欢迎垂询!
地点: 回龙观西大街85号琥珀天地608室
电话: 010-57186818